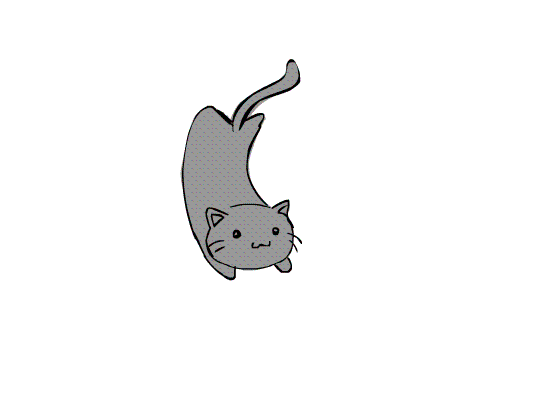在心理咨询室
在心理咨询室今天的来访者是个男孩,刚一坐下,他的第一句话便惊到我了“我害怕所有老师。”这是个怎样的男孩呢?
在这本属于课堂的时间,他又为何会来我这里而不去上课呢?为什么窗外不断传来鞋子踏在操场的声音与体育老师们的点名声呢?这宛如背景音乐般更好地解释了男孩的经历。
他后来什么都不回答,他一直一直看着我的鞋子以至于让我感到难堪。我反转了沙漏之后,他的注意力又似乎完全地集中在了沙漏之上,反正就是不看我的眼睛。他没有一次看过我的眼睛。
他还说,这么久以来,他连班里同学的长相都记不太清呢,因为他不敢看同学们的脸,之所以不敢看同学们的脸,是因为看向别人的脸时,往往会先看向别人的眼睛,看向别人的眼睛!天呐,他如此悲叹道,但是我根本看不清别人的眼睛。我的眼睛只是一片混沌,我的眼珠只有单调的棕色,我什么都没有。我没有白皙的皮肤,我没法写出一手好字,我没有动听的声音。
真的吗?他说。
他仍然清晰地记得自己被哪几个人夸过声音的好听,并始终如甘泉般珍惜地收藏那些美好的记忆,只在偶尔回忆,便甘之如醴。第一位是初一的时候,他第一次勇敢地在讲台上做了阅读的分享,对于开学几个星期了却还没有听过他的声音地女孩子们来说, ...
心琴
心琴河水仿佛冰冷的玻璃在流动。亚蒂恩布从马上下到地上,无边无际的水面仿佛延伸到另一个世界。沿岸布满了与河水仿佛一体的苍白的花朵,宛如一片小白花的宇宙,几乎已经将浅黄色的路面全然覆盖住了。亚蒂恩布望望河的对面,除了苍白的云朵默默地盘旋,除了惊起的飞鸟忽然的飞略,除了数十年前不见了的渔船在远处梦境似的地域迷航飘荡,亚蒂恩布什么也看不见。他只看见一片苍白色,一片苍白色,一片苍白色。
河的下游耸立着两座相望的白色高山,云朵如素带萦绕其上,山之间接着一小座木屋子,是一片冷色调中唯一的黄色,唯一偏暖的颜色。亚蒂恩布默然回头,身后的来路是一座绿色的巨大森林,绵延至远处绿色的高山,他正是来自那里,抛弃了家乡,跑起来了尊贵的王子的身份,仅仅为了探寻书中和年迈的魔法师临终前口中所说的世界的尽头的那把心琴(Heart of Piano)。她所演奏出的乐色绝不是东方珍贵的出现在诗人诗篇中的绿绮所能比拟的,抛却诗人夸张的因素,心琴才是真正的能够疗诊病痛的乐器。当心琴被纯白的乐手奏响,日月将齐升于东方。
亚蒂恩布沉浸于回忆之中。妹妹和母亲死后,他的孤单一直持续至今。
母亲死在那片广大的金黄色麦田之上,当时她正和 ...
求死的信念
求死的信念一叶独自地靠在冰冷的厕所隔间,冰冷的地狱。即使只有一叶一人,一叶也丝毫不觉孤单。就算身边有人看见血迹,看见星星点点的绽放一半的朦胧的血色花瓣,好像油渍迷迷糊糊地涂在毛玻璃上那样,朦朦胧胧地点在瓷砖上;好像远远天边将要坠落的云间的一个个小太阳。好像世界将要在太阳的坠落之中爆炸。他们也不会做出任何表示,他们的叹气声在行动者冷峻的眼里看来是多么虚伪,他们刚刚熄灭的玩笑声仍然在狭窄的空间回荡而回荡。他们说话后的空隙根本充满了畏惧的针。一叶看向刀片,红黑色的血迹松松垮垮地盖在银色刀片的尖端。刀是二十三号的手术刀片,不为别的原因,仅仅因为买的时候送了很多片,算上各种损耗,在一盒的美工刀片和四把修眉刀或者因为不小心掉进厕所,或者因为被收缴之后,唯一剩下的只有手术刀片,与硕果仅存的修眉刀。修眉刀太矮了,很难割深。手术刀可以割出令人骇目的伤口,在快割用力的情况下。十分疯狂。左手上红黑色的错综复杂的一道道伤口像极了美味的烤肉,令人垂涎三尺。一叶亲吻自己的伤口,探出舌头首先接触血液。是微甜的。一叶没法吸出更多的血,因为这两厘米长,一厘米宽的伤口根本不可能被称作“深”。这连轻微伤都算不上。一叶尝试舔 ...
五月十三日日记
脂肪是白色的,油脂是萝卜粒的橙,静脉是黑绿色
周日夜晚
惨月一镰禁天心,霜云散尽见月临
我度过了幸福的一生
我度过了幸福的一生精神病院是否类似为了预防犯罪而提前将病人逮捕呢?即使是所谓自愿,但人怎会有放弃自由的自由。人们怎能因为从未做过的事而付出代价呢?对于有危害性的精神病人,或许只能在他们发病之后审判了吧?令人头疼的问题。
在父亲的葬礼上我一点也不因为他的死而感到些许沮丧与悲伤,唯一印象深刻的只剩葬礼那令人生理不适的气氛,管弦呕哑,哭啼遍野。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一年级的七年间,我只有寒暑假会与他们相见。其他时刻完全可以用渺无音训来形容。或许在某个时刻,他被我远远地抛到幼儿园地童年了,整个小学里,接近我的只有爷爷奶奶。即使是在寒暑假,我也开始怀疑我对父母的笑是否是一种天衣无缝的伪装了,真笑与假笑的区别或许就在于,是否可以随心而立刻停下。现在我对母亲的许多笑,显然是主动的,受控制的笑。老莱娱亲似的。
存在回忆中的有几件事:低年级的我因为生气而回绝了跟母亲的许多次电话沟通,但随后收到母亲送来的塑料小兵人玩具时,愧疚与喜悦的并存似乎说明了我的生气同样是伪装的。伪装的情绪。因为听班主任说,某同学家长在外工作,便驱车数百公里而来学校开短短的一次家长会……班主任莫名其妙的赞扬令当时的我厚颜无耻地对母亲提出 ...
青春的色彩
青春的色彩如雨后初霁,远远天空上那缤纷的丝带,新生的阳光焕发着色彩。在人生起点的青春,谁将我们染上不同的颜色?我们自己。
青春是赤色的,如才撕开黑色混沌的天空中出现的朝阳,肆意的激情,向广袤的世界挥洒出无限的金光。我们还有着鲜明的梦想,还有着诗和远方,还有着改变一切的狂妄。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将自己深埋于书山,遨游于题海。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纵有巨浪滔天,承载梦想与希望的小舟不灭;漫天灰云墨雨,不能迷惘灼热的赤色双眼,相信奇迹一定会从远方,再次出现。赤色温暖的心中的火焰,让我们得以无畏于凌晨五点的寒冰飞雪,从床被一跃而起,就如此开始一天的学习。教室中的书声先于懒惰的太阳将世界唤醒,一片黑暗之中,我们仿佛带着光。操场上奔跑的我们不畏惧沾满脸颊的汗水与泥土,一串串飞洒的汗珠是活力的象征。
青春也是温暖的橘黄色。漫漫夜路里那守望在路旁的,一盏黄黄旧旧的灯,仿佛专门等待着你的到来而独自在夜中待了如此之久。这就是那温暖的友谊。当单薄的身体在寒风中颤抖,当无力的双手在冰雪中麻痹,当空洞的视线在白色风暴中模糊,友情便是远远的那等待着你,在飞雪中稳稳不动的那盏橘黄 ...
小故事三则
第一则她独自站在天台的边缘。摘掉了眼镜,灯火朦胧了远处的视线。灯火藏匿于身前,方形的玻璃与蓝色砖土之后。一只蝙蝠忽然飞掠,惊动窸窣的鼠群。
夜风吹起她的裙边,吹落她的身体,阖上她的双眼,吹走了这个世界。
第二则她是整座学园里最优秀的孩子,她简直就是光。任何场合下她总是最引人注目。她的座位在临窗的角落,阳光无时不洒向她的书桌,窗外无时不有夏季的白色飞鸟,低吟着各色的歌,次次飞过。
她当时微微笑着向老师与同学们的目光眯起右眼,左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圈,便笑着跳下了四楼,那声巨响也没能将那些呆滞的目光唤醒。
第三则夜已深了。她看看桌子左侧,唯一的灯火正在闪烁。书桌上摆着十二粒喹硫平,两瓶两百粒扑尔敏,二十粒舍曲林,十粒劳拉西泮,一百毫升的苯,一百毫升的乙二醇。
她想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且永远永远永远不会有人的地方。她如此害怕人们,她想要去没有人类的地方。她逼视着破碎镜子中狰狞的面孔,指责她的人说:“你去死。”
写于 2020.10.13 晚自习
对我自己的分析
隐隐得出的结论是,我的思想太复杂。曾将自己的一切行为视为对他人的否定,以至于存在本身也被视为一种罪过。叶藏便是在这种心态下,祈祷并离开纯子。不过在学校里我哪有离开的权利,因为我将离开学校也视为一种罪过——对他人的否定了。——一段内心独白:
“你们都很善良啊,待我真的这么好。但我为什么还会是这个样子?只能是我自己的责任了,没有一个人辱骂我,欺凌我,嘲讽我——诸如上述的一切无论客观还是我主观看来,都是你们从未做过的。但我处于痛苦之中的事实,我确信无疑。那么剩下唯一可能的选项便是我自己。一切的原因是我在精神自残。我只能白费你们的关心,而竟从未做出任何好的回应?虽事态在好转——我对你们坏的影响在一步步缩小。至少在行动上,我越来越透明。但我仍在恐怖着污染了你们的视线。于是不作为也包含着“存在着”这作为。我又在以“存在”这作为,来否定你们了。
世界是肯定的舞台。而我远远地躲在一角不敢呼吸,惊恐行为中任何否定的成分于是放弃行为。我的痛苦源自于对否定的不满足——存在,与自我肯定。否定否定的失败,否定在否定着除它自己之外的一切。
唯一对我影响较大的,PTSD的,也就2018年夏天,脑海中浮现出的那片黑色 ...
如何用叔本华的理论来解释叶藏
从来只是否定着自己的人畏惧他人的对自己的意志的肯定。因为隐隐透过个体化原理,他意识到这次对自己的肯定如此强烈。纵使这肯定不由他自己做出,这肯定亦增加了意志肯定的绝对值,透过根据个体化原理,这也是对于对方的否定,同时也是自己对于对方的否定。这是自己对于对方的,从前从来不敢做出的,现在却被对方自动做出了的,对他人的否定。叶藏的敏感将此视为杀人一般的罪行。于是叶藏在门后跪地祈祷着,被自己所杀的爱人可以从自己幻想的痛苦中解脱。为了避免自己做出更大的罪行————否定,而逃离。
叶藏隐隐看破个体化原理,于是被称作“神一样的孩子”。即使他们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推断写于 2020.9